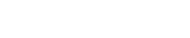1965年冬,我出生在陕北的窑洞里,据娘说,她生完我就晕过去了,醒来一看我安安稳稳躺在身侧,裹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破烂被子,棉花都露出来了,小崽儿闭着眼睡得香甜。
生下我之后,娘不明原因日渐消瘦,以前圆滚滚的肚子不见了,皮包着骨头架子,风一吹就倒,娘说她天生就不是享福的命,她想把仅有的福气传给我,希望我幸福平安。娘剪了一头齐耳短发,规规矩矩地垂在耳朵后面,她还像从前一样精干。
这次回家我没有提前告诉她,娘老了,接不了电话,也收不到信。
好久没有回去了,长大之后我们兄妹三人相继离开,在家乡之外的地方成家、生根,作为小崽儿,我离得最近,也更应该照料老娘,时至今日她仍一个人住在那窑洞里,平时种种菜,唱唱腔,自个扭个秧歌,不太和外人接触,父亲去世后,她似乎也跟着走了。
我在距离家500公里外的三原县城当公务员,那时回家需要两天时间,所以得早早出发。害怕我饿肚子,妻子提前备好了干粮(一角子锅盔馍)。回家的那天早上风雪交加,湿冷湿冷的,乡党们拿着大包小包,穿着厚厚的袄子往车上挤。汽车缓缓启动,载着我离开正在生活的小县城,回到娘的身边,去寻找细碎的光阴。
风随路途,月上枝头,从白雪遮掩的山峦之翠奔向一望无尽的苍黄土塬。离家更近,雪居然停了,云雾消散,星斗阑干分明,夜寒飒飒的冷寂里多了几分清新,汽车在路边停下,“下车咧,下车咧,今晚咱休息,明早上路。”司机一边扯着嗓子喊道,一边摘下自己头顶的棉帽子,赶乘客往车下走。
我刚从梦中苏醒,睡眼惺忪间,从怀中摸出那角子锅盔馍,把行李往座位底下塞了塞,随身带着个挎包走下车去。我知道这附近有个镇子,决定去看看,找个歇脚的地方,能避避风就好,其他倒无要求。没走几里路,看到一个饭店,牌匾在月光中显着木制的纹路,走近看刻着“福缘旅馆”几个楷体字。推开棉布帘子进去,一楼卖饭,二楼供人住宿,柜台在门后面,房间中间炉火烧得正旺,七八张桌子围着炉子摆放整齐,桌子旁坐满了人,其中不乏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和我坐同一辆车来,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又在这里相聚。
想着能睡得安稳一点,就选了个靠着墙的桌子坐下。在我对面坐着一位老者,顶着一头白色的蒿草,额头宽大布满皱纹,小眼睛藏在一副大大的石头镜下炯炯有神,嘴唇干裂微微张开,皮肤黝黑干涩没什么光泽。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酒壶,酒嘴儿从壶身侧面延伸而出,桌上有个小碟子,上面盛着一整块炒鸡蛋,分量不多约莫就一个鸡蛋的量。老头看到我坐到对面,权当没看见,自顾自地把酒壶拿到炉子边温了温,拿筷子把鸡蛋切碎,轻轻地夹起一小块,送到嘴里,然后再喝一口酒。酒和炒鸡蛋一下肚,老人脸上的皱纹微微舒展,浮现无穷的享受与满足。
作为一个基层公务员,我从未感受过酒的美好。酒辛辣、刺鼻,醉后让人头晕目眩,意乱神迷,喝酒应酬是我的工作,酒早已流经普通的生活,从每一个不省人事的夜晚渗进了我的骨子里。在这个回家探亲的冬日,看着老人喝酒,我兀然闻见酒香,问他可否给我到一盅,他二话不说递过自己的酒壶,努了努嘴,请我尝尝,我学着他也夹了一小块炒鸡蛋,喝一口酒,鸡蛋淡得没有味道,酒也凉了,但浊酒入口,深感无尽温柔,又喝了几盅,顺便把锅盔馍吃了,也分给老人一些,和他聊至深夜,沉沉睡去。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赶紧回到车上,检查了一下行李后在座位上坐好。我们兄妹几人一般是过年过节一起回家,今天突然到访,母亲一定会很惊喜的!在期待中,眼前风景不断变化,离家越来越近了。
窑洞大门敞开着,我径直走进去,菜园里落满积雪,狗窝废弃了,土狗来财不见踪影,院子里杂草丛生,房门半掩,烟囱里冒着白烟,炉子还在烧着。
“娘,我回来了,我想您了,提前回家看看!”我走进去。
母亲头发掉光了,陷在炕上喘着粗气,看到我来了,用干瘪的嘴唇发出近似孩童的喃喃呓语,气若游丝。
“强娃回来了。”

本文原载《JDB(中国)电子-官方网站报》第81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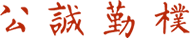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