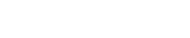关于邓小平系列谈判思想研究
卢山冰
摘要:邓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谈判思想。其中邓小平“国际原则与祖国统一实践的结合”、“谈判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邓小平处理与不同国家外交谈判的原则和邓小平谈判个性构成了邓小平谈判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邓小平思想 ; 谈判策略 ; 两个结合 ; 原则 ; 个性 ; 研究
国际原则与祖国统一实践的结合
——从“和平共处”原则到“一国两制”思想的飞跃
1.“一国两制”——和平共处原则从国际到国内的延伸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时由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在以后的中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并且业已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
邓小平同志在处理国际争端问题的有关谈话中,多次提到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而强调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诸如五、六十年代的“大家庭”方式和以后的“集团政治”“势力范围”以及各种“结盟”方式,都显示出其弊端,对于解决国际矛盾并没有多大益处。“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P96)。“一国两制”的思想在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会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中提出,当时尚未明确概括为“一国两制”。在两年后,在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时,邓小平同志明确做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概括。
在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同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话时,明确提出“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1](P30)而在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进一步讲道:“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1](P49)在当年十月份,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确定了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与“一国两制”的关系,“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1](P84)
2.“一国两制”——和平共处原则这一逻辑起点的必然演绎
邓小平同志从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到最后形成“一国两制”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基础到底在哪里呢?邓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的思维逻辑在哪里呢?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时谈话时指出:“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相处。”[1](P96—97)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下,可以解决好香港问题,对于台湾“问题也可以遵循这一原则”,“台湾当局提出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至少是太缺乏现实感了。能用一千几百万人口的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一一个一十亿人口的大陆吗?我们曾多次劝台湾当局,不要这样想,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1](P97)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处理国与国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和平共处原则”运用到处理国内事务之中,既务实地解决了随后的香港、澳门、台湾回归祖国的原则立场和大政方针,又从理论上解决了“一国两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体系。“一国两制”实际上是“和平共处原则”的逻辑延伸。
谈判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从“严格明确主权”到“共同开发”的谈判战略确立
邓小平同志明确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谈判时,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严格明确主权”与“共同开发”两种谈判战略。
1.严格明确主权论
在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上,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P12)“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1997年要收回整个香港”[1](P84—85)
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岁月》中回忆1982年9月23日与邓小平同志会谈时的情形时,不得不承认“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出乎我的意料。”[2](P417)“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2](P417)
在1983年9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换治权是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的局面。在英方一再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企图限制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更是将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与国家主权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看作享有主权的象征,“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风格果敢地坚持了香港的中国主权性。为随后香港问题谈判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在紧张和对抗不幸地笼罩着世界许多地区的时候,对香港未来地位的谈判取得成功,将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有效的,静悄悄外交的一次极为突出的首例。”[3](P367——368)
2.共同开发论
当今世界,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还有着许多存在争论的问题,从而导致国际纠纷和国际矛盾的出现甚至于矛盾激化。如何解决国际争端,为解决国际矛盾寻找出路,我为众多政治家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①借鉴“一国两制”,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
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2月22日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提出了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纠纷的构想。即把“一国两制”的模式借签到处理国际纠纷上,“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1](P49)在把“一国两制”模式推广到处理国际纠纷上,邓小平明确“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1](P68)
②在一些国际矛盾上“回避主权问题”,走“共同开发”道路。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1](P49)
1978年8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访华的日本园田首相双方讨论“钓鱼岛”问题时,初次提出了“共同开发的”设想。众所周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属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早在1972年9月,田中访华时,曾要求周恩来总理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总理明确表示“现在还是不讨论”。[3](P350)当日本田中首相再次提出“钓鱼岛”问题时,邓小平同志以大战略家的风度神态自若地指出:“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能接受的方法。”[3](P350)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之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其中进一步阐发了把“一国两制”的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上的思想。确认在处理某些国际争端时,有些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其具体内涵为:在中国与日本两国关于“钓鱼岛”的问题上,在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马来西亚、中国与越南关于南沙群岛问题上,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论,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1](P87)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而在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再一次强调了“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类似国际纠纷的谈判战略思想。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个性化谈判原则
——邓小平处理不同国家外交谈判的原则分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通过对国际形势的长期考察和冷静分析,对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的谈判原则指导。
一、非意识形态性谈判原则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的对外政策务际间的交流活动,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向后,邓小平同志力主并努力推动了中国全方位外交政策的落实。而开展全方位外交谈判的前提要求就是不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划线,“而是基于冷静考虑国家利益”。[2](P418)
1986年9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确信无疑地谈到:“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P168)在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又进一步强调尼克松在1972年访问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是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直到1990年,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一再强调,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加强往来,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要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P353)中国不在任何国家之间搞无原则的等距离交往,不去比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是从维护世界和平出发,按照每一国际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采取对策。
二、处理中美关系的谈判原则——“加强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中美两国之间自1979年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领域有了很多交流,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多次进行互访。在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以副总理的身份访问过美国,在增进两国之间的交流和了解上具有历史意义。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有三个文件,即1972年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国务卿签订的上海联合公报;1978年和1982年分别签订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公报和禁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公报,其中第三个文件尤其具有实际意义。在三个公报中,涉及到的中美关系上最突出的障碍,就是台湾问题。自5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领导人都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上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例如,自1981年1月里根总统就职到1982年8月中美双方就禁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达成协议为止,中美之间所进行的谈判共持续了六个月。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多次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这一协定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新框架。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也是坎坎坷坷。在美国对台湾的关系上,美国对华贸易和对华人权问题的干涉上,多次使中美两国关系陷入低靡状态。邓小平同志多次对来华访问的美国政界人士多次强调:“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1](P350)。在苏联解体后,对于来自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各种压力,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强烈反对,同时又始终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加强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谈判交往原则[2](P416),不断地推动着中美两国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
三、处理中苏关系的谈判原则——“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在八十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面临有三大障碍,这也就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中,中国提出的三个条件,即:减少苏联在中苏边界与外蒙古的驻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苏联放弃对越南的政治军事援助。
1986年当时82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虽然他年龄不小了,老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但是如果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问题解决了,也就是说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1](P169)
在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邓小平同志明确中苏两国会谈的目的和将来的原则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设:多做实事,少说空话。”[1](P295)邓小平同志对中苏关系的原则总结,成为以后发展中苏关系和后来的中俄关系的基础。
四、处理中日关系的谈判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依赖,长期稳定”
发展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邓小平同志会见的外宾中,以日本客人为最多。考虑到两国关系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状况,为使中日关系继70年代正常化之后,在80、90年代发展到新的高度,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双方应当在政治上不断加强相互信任,在经济上不断加强协作,使中日友谊能一代接一代一代好一代的传下去。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日两方制定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依赖,长期稳定”的中日交流四项基本原则。
五、处理中印关系的谈判原则——“一揽子式”
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在五十年代中期,两国曾有过很好的交往合作。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为世界各国处理国与国关系时所公认。
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会见印度外交部长时提出了“一揽子解决”原则。即中印两国在所有的分歧上都各让一点,就容易使问题得以解决。在1982年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进一步重申中印两国的分歧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国都有人民的感情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中国在与一些国家解决边界问题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双方相互让步,其经验完全可以借签到中印两国边界问题谈判中。
六、处理中国与第三世界关系的谈判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是邓小平同志为我国制定外交政策所提供的一个前提基础,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也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
邓小平同志认为,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中国完全尊重其他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遵循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是可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不能把第三世界分成进步的或反动的两部分,也不以他们对美苏的态度来划分。第三世界各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与任何国家保持密切关系,这并不影响我们同他们发展正常的交往关系。
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8月21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指出:“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1](P416)
邓小平同志认为第三世界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通过合作取得发展的愿望和条件。南南合作将会发展得很有前途,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必须寻求各种互相帮助的方式,才能够使第三世界国家更快地发展。为此中国除了给予一些发展中国家必要的援助之外,还争取把自己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重点逐步转移到以互利为基础的经济技术合作上来,并为此提出了中国在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中应该遵循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七、处理中国与东欧关系的谈判原则——“过去的事都不谈,一切向前看”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冷却了近20年。进入80年代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要向东欧开放,而且要同东欧加强关系。在与东欧国家政府和政党的交流谈判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过去的事情都不谈,一切向前看”的原则方针,提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要尊重对方的选择和决策,提倡建立党与党之间新型的交往关系。
严谨、坦言、幽默、务实与务虚结合
--邓小平谈判个性研究
邓小平同志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处理国内事务还是国际问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谈判个性。
一、 超常的记忆力
与邓小平同志进行过会谈的许多国际友人,都对邓小平同志很强的记忆力佩服不已。正如哈默博士在《勇敢的人――哈默传》中所述:他非常敏锐,非常明智,而且,正如我以后发现的,他有着很强的记忆力――每次和我见面他总是确切地记得前一次都讲了些什么,他从不需要笔录或问他的助手。他总是什么都知道。
早在1979年2月,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在美国南部新兴工业城市休斯敦的一个盛大欢迎晚会上,他与哈默博士初次相识。当译员按照惯例向邓小平同志介绍他的经历时,邓小平同志止住译员的话,对哈默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访问。”[3](P262)这位曾帮助列宁的“红色资本主义家”从此开始了与刚刚改革开放中国的合作。
邓小平同志在与国内有关负责人谈话和国际友人的会谈时,许多重要的数字和历史事件几乎都能脱口而出,而不用助手或翻译提醒。他也从没有拿讲稿的习惯。直到他八十几岁高龄与外宾会谈时的有关谈话,都显示出了他清晰思路和很强的记忆力。
二、 语言的严谨与条理性
邓小平同志谈话和谈判中的语言条理性是他极为显著的特点。而其中尤其以“三点”和“四点”为突出。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多次外交谈判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三点。第一,十年动乱已经结束,而且不会再重演;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2](P129)邓小平同志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也讲道:“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989年9月4日在谈到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局势中国的应对策略时,邓小平同志概括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
纵观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其思维的逻辑性无不在其讲话的条理性中充分体现出来。
三、 思想的高度概括性
邓小平同志在与国内人士和国际人士会谈时,又非常注意思想的概括性。比如,对于前一段工作的概括性总结,对于两党关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概括,对于两国关系的总结和展望,都经常做出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在前面我们所做的分析中,可以明确发现这一特性。如在处理中苏关系的谈判中提出的“忘掉过去,开辟未来,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谈判中提出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依赖,长期稳定”,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谈判中提出的“加强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在处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外交谈判中提出的“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在处理中国共产党与东欧各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谈判中确定的“过去的事都不谈,一切向前看”等原则,都因其高度概括性而成为以后中国处理与这些国家(或政党)在处理双边关系时的原则。
四、坦率直言、刚正不阿的性格
与许多政治家与对手接触中多采用说服的和间接的方法不同的是,邓小平同志总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其对手,在有关原则性的问题上无所畏惧地争论,勇于敢于正视,甚至公开彼此之间的分歧。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邓小平同志是“棉里藏针”。在中日、中美、中苏等两国领导人会谈中,以及邓小平同志多次与国内外友人会谈时,都表现出他在原则性的问题上的直言不讳的性格。例如,1983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国务卿、里根特使舒尔茨时,据实抨击了里根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的霸权行径。邓小平坦率而又严肃地对舒尔茨说道“前不久,美国司法机关公然企图‘传讯’中国政府,这是典型的霸权行径,真是岂有此理!请特使转告里根政府,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受侵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3](P267)
在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直言不讳地谈道: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后延续到苏联。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谈判合理解决这些边界问题。在谈到中苏两国的交往上,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地讲道:“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帐,我们提前两年换清了。”[1](P294)“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1](P294——295)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家政治领袖的胆识、雄魄和气慨。
五、谈话风趣幽默性
在西方国家领导们的眼中,邓小平个性表现为:果敢、自信、刚毅和幽默。
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对邓小平同志谈话的幽默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实力与原则》一书中写道“邓小平在访问国会时,谈话生动幽默,留下很好的印象”。[3](471)美国东西方中心主席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在《回忆邓小平》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邓小平“处理问题果断,不乏机敏的幽默感”。[3](P479)当布垫津斯基向邓小平询问中国是否有人反对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很快回答说:“有”,稍停片刻之后,接着说“台湾有人反对(关系正常化)”。当卡特总统想了解中国是否将允许向外国移民从而符合杰克逊――瓦尼克法的标准和达到最惠国条件时,邓小平诙谐地答道:“我们非常了解你们的法律,这不成问题,你们想要接纳多少中国人?1000万?”,邓小平同志以幽默的语言回答,巧妙地中止了卡特总统的这一话题。
六、强调务实和务虚相结合
邓小平同志日常工作中一大部分工作是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重要的国际友人。在这些会谈中,邓小平同志一方面与这些来访者“务实”地谈论一些双方共同关心的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利用这样的外事场合,公开向外界介绍、解释当前国内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具体的解决政策甚至一些思想动态。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119篇重要讲话、谈话文章,就有69篇文章是在会见国际友人和港台知名人士的谈话。其中每个谈话都实事求是地对于国内的一些情况进行了宏观介绍,对于实行的政策、方针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进行了一定解释。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在这些谈话和讲话中都有很多凸现、丰富和完善。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中的具体思想的产生背景,也对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有了一个清楚认识。(本文获得JDB(中国)电子-官方网站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教工组二等奖,作者为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引文: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下)——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
[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2]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上、下)——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陈先奎著:《为邓小平辩护》,西苑出版社1999年版。
[5]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向洪文主编:《邓小平军事谋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原著: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伊文思,武市红等译:《邓小平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宗峻著:〈〈总设计师〉〉,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编辑:田明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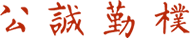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